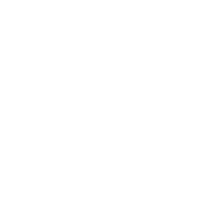不思量自难忘抒情散文
这几天老是无眠。窗外不时飘落的树叶,在昏黄的路灯下,斑驳成碎片,思绪也如这落叶般,飘摇、零乱。人生匆忙,也许不该也不能牵挂太多,然而有些事情,却总是“不思量,自难忘。”表哥伟伟,大我两岁,是五舅舅的儿子。五舅舅是四外婆带养的,我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小时候,我俩经常在一起玩耍。听大人们讲,几岁时的我,伶牙俐齿,特别逗人喜爱,一到外婆家,表哥表姐都会围着我转。伟哥哥长得虎头虎脑,更像保镖一样左右陪着。有年正月,我又到了外婆家,伟哥哥一见到我,转身跑回家,拿来一个崭新的布娃娃,放到我手里,低声说:“胜胜,怎么这么久不来?害得我把新玩具藏了好久呢。”那个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玩具是很稀奇的。表哥表姐们望着我手上的布娃娃,眼睛发亮,一窝蜂似的围了过来。布娃娃被大表哥抢走了。伟哥哥急得红着眼睛,小拳头乱舞,拼了命似的从大表哥手里抢回布娃娃,放到我手里,叫我攥紧。小表妹们吓得“呜呜”大哭,五舅妈开玩笑似的骂道:“伟伟,布娃娃为什么不让其他弟弟妹妹一起玩呢?你这么讨厌,长大后肯定会讨不到媳妇的。”这时,伟哥哥硬起脖子,涨红着脸说:“我将来才不找别人,就找胜胜当我媳妇!”话音刚落,在场的人哄堂大笑起来。此后,只要我和伟哥哥在一起,大人们就拿这事笑话我俩。
那时,我们懵懂无知,对大人的这些笑料根本不在意,也不去理会。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去外婆家,依旧和伟哥哥整天粘在一起,摘野果,翻螃蟹,玩游戏……无忧无虑,度过了幼年时的快乐时光。
渐渐地,大人们眼中的这对“金童玉女”长大了,也谙事了,而我们在一起玩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还故意躲着不见面,偶尔遇见,也会面颊发烫,低头侧身而过。可不知怎的,我心里又盼着能见到伟哥哥。朦朦胧胧中,我意识到了一点什么,这常常让我独自害羞。
和伟哥哥的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八七年正月。表哥结婚,我们一起去喝喜酒。那天,正下着鹅毛大雪,亲戚们都围坐在堂屋里烤火,谈笑。这时,八舅妈指着角落里一双沾满泥巴的白色球鞋对我说:“胜胜,去帮我把那双鞋洗干净吧。”我尽管不愿意离开火堆,还是欣然答应。当我冻得红紫的手提着干交给八舅妈时,她却笑而不接,随后便听到满屋笑声。
我不知所措,抬头看见伟哥哥满面通红地朝我走来,接过我手里的鞋,窘迫地说:“谢谢!”。原来是八舅妈开我的玩笑,其实那双球鞋是伟哥哥的。我羞得面红耳赤,低着头,跑出了堂屋大门……
雪还在下着,纷纷扬扬的,飘舞在村子的上空。屋檐下的冰棱,晶莹剔透,如少女凝结的一段段心事。除了雪花飘落的声音,四围银装素裹,是那般静谧。踩在雪地上,“吱吱”的声响像悠扬的音乐,心情愉悦而欢快。想起刚刚八舅妈开的玩笑,脸上又火辣辣的,怀里像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
转回来,一进堂屋,又看见伟哥哥坐在那,我故意视而不见,偷偷转头,却发现伟哥哥正看着我,一种我从没见到过的炽热目光,像一团火,我感到自己的心扉顷刻被照亮了。从那时刻起,伟哥哥那如火一般的目光就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
我在外地学校读书,月末回家一次。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老感觉心跳加速,烦躁不安。妹妹老远跑来接我,欲言又止,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拉着妹妹的手说:“有什么事?快说!”妹妹小声说:“姐,伟哥哥早几天得出血热,被医院误治……走了。”当时,我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泪水像开了的闸门似的倾泻,嘴里语无伦次地念着:“不,不可能,他……怎么可能……”那些日子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伟哥哥的一颦一笑,就出现在眼前。迷迷糊糊睡到清晨,起来时,枕上常湿漉漉的。
那年,伟哥哥十六岁,已是一米七八的英俊少年。他彬彬有礼,人见人夸,成绩也十分优异,还当上了学校学生会主席。在乡下,这样优秀的少年是少有的,亲朋戚友无不为他惋惜。出殡那天,很多老师同学都去了,灵堂里一片哭声。生命怎么如此脆弱,如此短暂,伟哥哥就这样永远地走了,走得这般匆忙,这般无情,永远地离开了父母亲人,也离开了我……
其实那时,五舅舅和母亲早已替我俩想好了报考的学校,我考卫校,伟哥哥报农校。也许,大人们心里还埋藏着对我俩以后的什么想法和安排。然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没有了意义。第二年,我顺利地考上了卫校,高兴之余,我又深深遗憾着……
去卫校的第一个晚上,我独自来到空阔的操场。高远的天空,朦朦胧胧,星斗隐约;四周树影依稀,夜虫鸣叫。我静静地走着,想从这陌生的环境中,寻找心底的想往。遥远的天际,一颗流星划过,好美的,却又倏然不见了。我突然想起了伟哥哥,想起了我们曾经的青梅往事,想起了他对我的种种好。我知道他对我的好,是朦胧又最美的情愫,是一种心灵的默契,是一种人世间最难遇见的圣洁……
总角青梅的感情,是最刻骨铭心的。一个野花绽放的`季节,天阴霭霭的。我和伟哥哥在外婆家旁边的小山上玩,看见陡坡下有一朵黄色的野花,我很是喜欢,可是手太短,根本采摘不到。伟哥哥看着我,让我一手抓住旁边的藤蔓,一手拉着他的手,他慢慢地下到陡坡去摘花。或许是我的力气太小,或许是地面滑,就在他伸手刚摘到花的那瞬间,我拉着他的那只手突然伸开了,伟哥哥滚下了几米高的陡坡。我吓坏了,急得在山上哭着喊着,却又找不到下去的路。伟哥哥在坡下吃力地站起来,大声安慰着我。然后跛着脚,艰难地从陡坡爬上来,把小黄花插到我头上,还用手抹着我脸上的泪水说:“你戴着花几多好看的,哭什么嘛,我的脚一点也不痛啊。”我看他咧着嘴,脚背上流着血,便赶紧蹲下,用衣襟去捂他的伤口。这时,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雨水湿润着我的脸,也润湿了我那颗小女孩的心……
我默默地站在操场上,夜已深,身上有了些凉爽的感觉。天际依然是朦胧的一片青蓝,星光遥远闪烁,仿佛是伟哥哥的眼睛,深情幽幽地看着我,关注着我。后来,当我在人生旅途上艰难跋涉,得意或失意时,我总感觉有那火一般炽热,星一般深邃的目光,伴随并鼓励着我前行。我想,我曾经拥有一份少年的圣洁与知心,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和财富。时间如白驹过隙,我还奢求什么呢?相遇是一种偶然,离散何尝不是一种必然,只要曾经感知过,感受过,不也足够了么?
二十多年过去,我和伟哥哥,纵使相逢应不识吧。伟哥哥,你在那边好吗?此刻,眼前已是一片模糊。这么多年了,我努力不去想,却还是不能忘却,还是不能释怀……
不思量自难忘抒情散文
这大概是苏轼写过最痛的一首词了吧,字字啼血,句句刻骨,历历在目。
是啊,这世间,又有什么距离能抵的过生死相隔呢!人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即便是再温暖的回忆,都会变成剜心的刺刀,每回想一遍,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更要命的是,那些对过往念念不忘的人,还偏偏乐此不疲。
如果用你的五年,换一个人的五分钟,那个人会是谁?
明知道这种问题最没意义,就算有那个人,又能怎样呢?但你的脸依然那样毫无防备的浮现在脑海里。
如果用我的五年,换你的五分钟,你愿意么?
就算贪心也好,我想和你一起,把我们以前每天要走的路都走一遍。我想和你一起,吃放了许多辣椒的蛋炒饭。我想和你一起,走两三公里的路去上学。我想和你一起,看整整一个下午的奥特曼……
我想和你一起,做什么都好,只要是你就好。
你看,不是说人忘七年么?可我好不容易等到那个所谓的第七年,为什么还是忘不掉你呢?或许,都是骗人的吧。你是个优秀的孩子,那个大家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这是在你离开后我才后知后觉醒悟的。初春的风总是来势汹汹,把窗子吹的呜呜做响,你一个人专心致志的玩着你用废弃木块自制的玩具车,嘴里模仿着大卡车发出的声音。那声音和风声和在一起,我老是分不清那是风还是你。初春的风依旧很大,还是总会吹乱我的头发,可风里没有你的声音,也没有你天真烂漫的表情。
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又开始留长发了。虽然你从未见过我短发的样子。我还是会经常想起你,在路过那些稚嫩的面孔时。说不上有多撕心裂肺,只是会隐隐的疼一下,脑海里不自觉的出现你的笑脸。后来啊,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都没那么痛了。我总在想,如果你还在的话我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和以前一样,老是像我撒娇,要我骑着自行车载你去爷爷奶奶家?会不会还是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在路口等我回家?会不会还是一边吃一边吐槽我做的蛋炒饭味道不对?会不会还是那么懂事,每天晚上都会自己把作业做完才去玩?会不会还是会和我谈条件,说考第一就让你看一个假期的铠甲勇士?虽然你老是考第一,但遥控器还是抢不过我。呵呵,应该不会了吧,毕竟如果你还在的话,就十七岁了。十七岁,本来该是多么美好的年纪啊。和别人一样,美好的年纪。
你的十七岁,会做些什么呢?应该会有自己的小心思,应该会有暗恋的女生,应该也会和别的孩子一样偶尔会有点小叛逆,也会向我发发小脾气。
要是能这样该有多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活着该有多好。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偏偏你就不行呢?
你还有那么多事来不及做,还有那么地方来不及去,还有那么多人来不及遇见,怎么就舍得丢下这个世界?
以前我不信命,因为你,我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