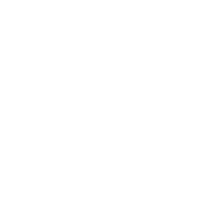比较政治学方法篇1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610500)
摘要:对成都市社区居民的调查发现,社区政治参与活动的组织力度不够、效果亦不甚显著;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不高,主要内容是“选举”,主要方式是“组织参与”;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与其行动参与度“一般”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尚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社区;社区参与;社区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F6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7.0036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首要任务是和谐社区的建设,和谐社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要求社区建立一个与居民有效互动的联系模式,良好的互动则建立在居民积极的社区参与、尤其是政治参与的基础上。政治参与是社区参与的主要内容之一,体现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是当前我国社区参与的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从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内容与方式两个方面,考察其社区政治参与的现状与特征,尝试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为和谐社区的建设提供有力的实证材料。
1调查概况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成都市的社区居民,以个别发方法来收集资料。对于样本的抽取,首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成都市金牛区、武侯区、新都区3个区,在这3个区内分别抽取2个社区,最后按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调查于2015年1月进行,共发放问卷650份,收集有效问卷631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7.1%。对收回的问卷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码,然后输入数据库;经过查错和修正,确保了统计数据的准确可靠;最后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和推论性的统计分析。
调查的样本组成情况(见表1)显示:性别方面,男性的人数比率占59%,比女性的高18%;这个比率较为适中。年龄方面,被调查者中青年(18-34岁)的比率最高,占近60%;其次是中年(35-55岁)者,占近1/3;老年(55岁以上)、少年(18岁以下)者的比率均较低;可见青壮年的人数居多。民族方面,汉族占绝大多数,人数比率占90%,远高于少数民族者,另有1.9%的人未答。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及以上、高中/中专/技校、初中者的人数比率居前三位,小学及以下者的比率相对较低,不足17.5%。婚姻状况方面,已婚者的比率最高,占近49%,比未婚者的高10.7%;离异、丧偶者的比率较低,均占6.5%左右。政治面貌方面,群众的人数比率居首,占近58%;其次是共产党员,也占30%;共青团员和民主党派者的比率很低,均不足6%;5.9%的人未答。职业方面,民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的人数比率最高,超过1/4,比商业/服务业人员、务农或打工者分别高5.2%、6.9%;失业/待业者、离退休者、学生的比率较低,均占9%左右;其它职业者的比率更低,均不足3.5%。家庭人均月收入方面,选择4001-5000元、3001-4000元、2001-3000元的人数比率居前三位,均占18.5%左右;其次是1001-2000元、1000元及以下者,也占13%左右;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各阶段者的人数比率均较低。
2成都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组织现状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政治参与的主体,其具体参与行为与组织活动(如宣传、动员等活动)状况密切相关,文章主要从相关部门组织社区政治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行动力和效果着手,考察该方面的基本情况。
对于“相关部门组织社区政治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调查结果(见表2)显示: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一般”,人数比率占52%;其次是认为“组织积极”(包括非常积极和比较积极)的,占近36%;而认为“组织不积极”(包括不太积极和不积极)的比率相对较低,不足12.5%。可见,被调查者对该工作组织积极性的评价不高。
对于“相关部门组织社区政治参与活动的行动力”,调查结果(见表3)显示:超过51%的被调查者认为“行动力一般”;其次是认为“行动力强”(包括很强和较强)的,也超过30.5%;认为“行动力弱”(包括较弱和很弱)的比率相对较低,不足18%。可见,被调查者该活动行动力的评价不高。
对于“相关部门组织社区政治参与活动的效果”,调查结果(见表4)显示: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效果一般”,人数比率超过56%;其次是认为“效果好”(包括很好和较好)的,也超过30%;认为“效果不好”(包括不太好和很不好)的比率相对较低,不足14%。可见,被调查者该活动组织效果的评价亦不高。
3成都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行为现状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本文中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则界定为社区居民以各种方式参与本社区内部政治活动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足44.5%的被调查者表示参与过社区内政治活动,多数人则表示“没有参与”,可见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状况不甚理想。在参与过社区内政治活动的被调查者中,进一步考察其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与积极性三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对于“选举”活动,绝大多数人表示“参与过”,人数比率超过70%;对于“社区居民大会”,超过1/3的人表示“参与过”;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等学习活动”、“党的方针政策等学习宣传”、“发展党员活动”,表示“参与过”者的人数比率相对较低,均占14%左右;对于“上访”,只有不足3.5%的人表示“参与过”。可见,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内容是选举活动。
对于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方式,选择“组织参与”者的人数比率最高,占近48%,比选择“组织与个人参与结合”的高8.5%;而选择“个人参与”的人数比率相对较低,仅占13%。可见,组织参与是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对于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绝大多数人表示“积极”(包括非常积极和比较积极),人数比率超过66%;其次是“一般”的,也占近1/4;表示“不积极”(包括不太积极和很不积极)者的人数比率很低,不足9%。可见,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
4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成都市社区居民认为相关部门组织政治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行动力不强、效果不明显,整体组织工作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有许多尚待努力与改进之处。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活动是“选举”,其次是“居民大会”,而其他社区政治活动则很少参与;“组织参与”是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应继续大力提倡和加强;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高,与其行动参与度“一般”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可见,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情况总体不甚理想,尚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通过对成都市6个社区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初步了解到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组织与行动基本情况,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但同时也存在不足,由于经费、人力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样本的抽取仍未按照严格的概率抽样方法、样本规模也不大,因此结论的覆盖面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
参考文献
1梅志罡,李文献,黎园.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城市基层社区自治管理研究——以武汉市社区协商民主情况为例[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2)
2雷勇.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
3胡琦.论社会组织对政治参与制度化的作用[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12)
4曾凡斌.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200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数据[J].现代传播,2014(10)
比较政治学方法篇2
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不过很难对比较分析作简单界定。界定比较研究法涉及诸多复杂问题,例如社会科学领域比较研究的可能性;恰当的比较单元(国与国比较、地区与地区比较、或其他单元的比较);比较研究中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①。简单说来,比较分析涉及时间和地点两个维度,包括两种类型:同一历史时段内一国内部各种单元的比较;同一历史时段内不同国家的比较。一些历史学家按照历史学界的惯例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比较排除在比较历史学的范围之外②。沿用这一标准,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③也不能算是比较政治学着作。这一判断与人们对比较研究的理解相悖。此书研究南北意大利“公民能力”(civiccapacity)的差异,进而对比两个区域的政府绩效,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比较对象是一国内部的两个区域④。如果按照常用意义使用“比较”一词,一国内部不同单元的比较也应该属于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一种“比较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这种“比较分析”其实属于历史研究法,本文讨论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时不考虑这一类型。
一、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诸领域的应用
比较分析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不同。出于方便论述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政治学研究分为三大领域:第一,政治理论构建⑤;第二,外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第三,本国政治理论与实务研究,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国政治研究。第二和第三两个领域中的政治实务可以简单理解为一国政治制度及其运转,政治理论则包括精英的政治思想和大众的政治观念①。这里的三分法并没有穷尽政治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例如,它没有涵盖国际政治。此外,具体研究通常不可能分成这样的三类,一项研究可能同时涉及这三个方面。为了方便论述,本文所区分的本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不是截然分开的。研究一旦涉及本国与外国比较,无论这种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研究者对本国的认知与对他国的认知必然相互影响,套用后现论的术语,此时,个体或群体对“自身情境”和“他者情境”的认知相互“构建”(construction)。对于三分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政治实务”、“政治理论”这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是聚讼纷纭的话题,即使按照经验和常理对它们进行广义界定,政治学研究必然还会涉及“政治实务和理论”之外的领域,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就远远不限于“政治实务和理论”。三分法大大简化了政治学研究的复杂性,有诸多不足。尽管如此,这里划分的三个领域还是凸显了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对探讨比较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失为有用的出发点。(一)政治理论构建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首先来看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理论的构建。在政治学发展史上,有一类研究属于纯粹的理论构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研究”。例如,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无论二者的论题和分析路径有何差别,它们所构建的理论体系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抽象的、成体系的理论”。《法哲学原理》和《正义论》中的理论构建并非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分类与比较,这些理论是从若干个预设规范推演出来的,比较分析在这一类研究中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对于另一类以归纳法提炼理论的研究工作,情形可能有些不同。此时,理论构建的前提是对同类现象的比较。由此看来,比较分析对于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的构建不可或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政治学界提出的“民主化理论”是“实证型”理论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开始从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哪些条件有利于或不利于朝向民主的成功转型以及转型之后民主制的巩固?20世纪下半叶拉美、东亚、南欧,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等区域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呈现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同的转型模式?“民主转型与巩固”(democratictransformationandconsolidation)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发展起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跨国比较是一种有用的方法②。(二)外国政治研究在实证研究领域,比较分析对于理论构建至关重要,这么说应该不会引起多大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种方法在国别研究中的作用。从表面上看,研究一国政治毋庸比较。这种说法对于未受过现代政治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来说是成立的,因为他的知识仅限于对本国的了解,他对异邦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不会采用比较分析法。一旦研究者的知识涵盖本国与外国两个方面,比较分析就成了他研究时无法摆脱的“魔咒”。下面回到上文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个方面:外国政治实务与理论研究。研究者考察外国时即使没有直接采用比较分析,他往往也会“潜在”地进行比较:与本国比较、与他所知道的其他外国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民主的那部名着其实也是一部采用比较研究法的着作。踏上美国之前,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已经知道美国之行所要解决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Saint-Beuve)说:“托克维尔在他一无所知时便开始思考。”事实恰恰相反,应当说:“托克维尔去美国寻找法国问题的答案!”《论美国的民主》通篇谈论美国,托克维尔思考时却总是把美国与法国进行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并没有直接在文本中呈现③。托克维尔在写给一位将要去德国考察的朋友的信中对“潜在比较”的作用作了精彩解说:向法国读者描述一个社会的整体图景是个难题,这个社会的精神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困难不仅源于这个社会实际如何与我们认为如何不一致,我们对自身的体认引导我们去想象,这才是症结所在。偏见自然而然地产生于我们对祖国的反思和对本国历史的记忆,它对比较研究造成的困难远甚于我们研究时的疏忽。我不知道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唯一可做的是请您想一想自己对德国最初的认识以及后来理性的认识,再想一想如何一步步从最初的认识过渡到后来理性的认识……您想解释德法两国的异同吗?还是想让读者从您的作品中自行发现答案?……我研究美国民主时一直采用后一方案。我很少提到法国,但我写下每一页时无不想到她,她仿佛就在我面前。我并没有试图描述和解释美国这个异邦的方方面面,我只想指出她与我国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认为属稿过程中不断地联想法国是这本书成功的根本原因①。据上述引文,研究外国时比较分析有其特定困难:(1)研究者对他国的认识与该国的实际情形不一致;(2)研究者所处的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会制约他对其他国家的理性认识。托克维尔认为后一重困难对比较研究的影响更大。《论美国的民主》采用一种特殊的比较研究,参照系并没有在文本中彰显。托克维尔采用这种方法要实现双重目的:通过比较来理解法国;利用美国、法国等个案,探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如他主张,“为了理解下文,视野必须越出法国;任何人如果只研究法国,我敢说他将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②“把基于美国和法国社会的概念作为我的出发点,我试图描绘民主社会的一般特征,对于民主社会,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模式。”③推崇托克维尔对比较分析的成功运用时④,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比较分析的消极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时应时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国政治的运转有其“内在逻辑”,研究该国的首要任务是把握这种“内在逻辑”。比较有助于研究者探究这种“逻辑”,不恰当的类别也可能会遮蔽这种“逻辑”,这重危险可以叫做比较分析的“遮蔽效应”。进行比较时如何避免“遮蔽效应”是考验研究者技艺的难题。第二,托克维尔所用的“潜在比较”可以看成一种为解决本国问题而研究他国的策略,这种方法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相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与“价值中立”并非总是冲突而不可调和,然而研究如果完全为现实关怀所左右,对外国的考察服务于预定目的,这样必然不利于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这里出现了目的决定结果的现象,可以称之为比较分析的“诱导效应”。研究从一种预定目的出发,凡是有利于此目的达成的证据都被放大,凡是不利的证据都被忽略乃至改动,比较分析成了一张过滤之网;运用这张过滤之网,能够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可以纳入“美国模式”。我国学者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批评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不余遗力,通常的批评是西方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带着偏见和政治目的研究中国⑤。勿论这类指责是否成立,它确实揭示了研究时应当尽力避免的一种倾向:研究外国时(有意、无意地)与本国对比,对本国(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支配着对外国的观察。比较分析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可能产生“遮蔽”或“诱导”效应,但不能因此否认比较分析对国别研究的价值。即使仅仅研究一个国家,研究者持有比较的眼光,也有助于他提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比较使研究者更加敏锐和更具洞见,比较催生灵感,比较分析的重大价值即体现于此。(三)本国政治研究上述讨论也适用于本国政治的研究。考察一国政治,忽视该国政治的“内在逻辑”;研究者在本国政治社会情境下产生的问题意识左右着对外国的考察,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本国政治研究中也可能出现。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时简单类比他国事例,这么做岂非忽视中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潜在地以某国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这么做难道不会扭曲对中国情形的体认?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潮:“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两种思潮的鼓吹者都通过中西比较提出关于中国发展方向的结论。“西方”在支持“中体西用”的人看来是反面标准;对于“全盘西化”论的信奉者来说,“西方”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中国人凭借西方资源反观本国时认知扭曲的突出例子①。上文讨论的比较分析对国别政治研究的积极意义当然也适用于中国研究。下面挑选三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分析能够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这三个例子涉及三个重大课题: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还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基层自治。推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疆域辽阔,加之传统社会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这使得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异常困难。国家对基层的管理要依靠地方士绅,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皇权不下县”———某些基层区域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间。现在随着微观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科学界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审视的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人再也不能把上述“基层自治说”当成定论而无条件地接受了②。“自治说”之失在于对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化。国家控制与地方(或基层)自治并非截然对立,探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一些学者引入“国家内卷化”的概念就是有益的尝试③。研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推进。如果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看,“自治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古代实行城乡合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存在“自治共同体”。与中国的情形相反,欧洲国家有城市自治的传统,城市自治权是一种“法权”。城市所隶属的国家———无论推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可以向城市颁发“特许状”,从而授予城市自治权,但是国家不能随意收回或缩减这些特许权,否则将激起城市针对国家的抗争④。反观中国古代的情形,城市共同体和乡村共同体并不享有“自治法权”⑤。国家可能容许地方共同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不过这种权利并非保留给地方,国家可以随时侵入地方的“自治”空间,并且只要国家愿意,她总有可依赖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种制度资源来实现这种入侵。地方士绅作为国家的维持地方秩序,他们不像欧洲城市自治势力那样为确保地方自治而对抗国家。中西比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实质。可以把上述比较概括为两种中央地方关系类型的比较,在欧洲,地方构成国家;在中国,国
比较政治学方法篇3
由此我们可以列出中国语境下讨论政治参与的主要问题:(1)动员和主动的比较:由政府或其他团体和个人赞助、引导或强迫的政治活动应被视为政治参与吗?或这个概念应被设定在普通公民自愿参与的政治行为?(2)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的比较:政治参与包括那些非法的政治行为?还是限制在合法的政治行为上?(3)政府的和非政府目标的比较:政治参与应局限在政府权威、政策和制度范围内的行为?还是也包括政府范围之外的行为?针对以上所罗列的几点,无论是国外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都有较大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仅关于其概念本身的界定,也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中国语境下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第一,关于主动和动员的比较,几乎所有关注政治参与的学者都给出自己的答案。简单梳理国外学者的观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政治参与不应包括非自愿性的政治行为。在维纳看来,一些非民主国家,采取操纵性的办法,发动人民宣誓效忠、强迫人民投票,这些非自愿的政治活动并不能视为政治参与。〔16〕而维巴更是将动员性的政治参与称为“礼仪性参与”(ceremonialparticipation)和“支持性参与”(supportparticipation)。在他看来,虽然很多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学者都将动员性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参与的范畴,但是这种被动的政治行为事先就被限定在既定的政治选择和“统一的国家利益”之中,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并不能真正发挥其影响力,而“它(政治参与)强调群众源源不断地释放出的影响力,特别是,它不要求支持先前存在的统一的国家利益,它是创造国家利益的过程的一部分”。〔17〕另一部分国外学者则认为,政治参与不仅包括依照自己的意志自主参加的政治行为,而且也包括受他人动员、诱导甚至逼迫的政治行为。
陶东明和陈明明认为,“从参与的途径上讲,……(政治参与)可以是组织的(动员的)参与或自发的参与”。〔20〕王立京认为,“我国政治参与研究应该对动员性参与给予相应的重视,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本土特色和应用价值”。〔21〕而陈振明和李东云则将中国语境下政治参与涵盖动员性参与和自愿性参与的理由归纳为两点:首先,“那就是我国以往计划体制下存在广泛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型参与,值得加以专门研究”。其次,“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动员传统和政府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也是今天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政府持有的一项重要资源和特别优势”。〔22〕第二,关于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的比较,国外政治学者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部分国外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参与的概念应该被限定在合法行为的范畴之内。维巴认为,包括骚乱、暗杀和其他类型的公民暴力行为虽然也会对政治产生影响,但其属于另一个研究题目,所以政治参与的“最后一个限度是:我们关心的是‘体制之内’(withinthesystem)的活动———影响政治的合法手段”。〔23〕而另一部分国外政治学者则将非法行为包括在政治参与的范畴之内。“我们把政治参与定义为试图达到上述目的的所有活动时,并不考虑这些活动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准则是否合法。因此,抗议,暴乱、示威游行甚至那些企图影响公共当局的叛乱行为,都属于政治参与行使”。〔24〕至于将政治参与的范畴扩展到非法行为的理由,巴恩斯和凯思在《政治行动:五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群众参与》一书中认为,非法的政治行为同样体现了普通公民影响“政治抉择”的意愿,是合法政治行为的“一种政治补救方法”,“他们特别坚持说,政治参与的概念应包括抗议和暴力行动,这样才能对美国和西欧的政治作出适当的解释。”〔25〕对于政治参与是否包含非法政治行为的争议,国内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政治参与不应该包括非法的政治行为。周少来认为,“从政治参与的方式看,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合法方式进行的影响活动都属于政治参与,如听证、集会、游行、上访等合法活动,但不包括以非法暴力方式和恐怖活动试图影响政治运作的行为”。〔26〕王浦劬认为,“从政治参与的外延来看,政治参与只局限于合法手段影响政府的活动,而不包括非法的行为……如果将政治参与的外延扩至非法的暴力活动,政治参与和政治斗争两种行为就很难区别开来”。〔27〕但是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
陶东明和陈明明认为,“从参与的途径上讲,……(政治参与)可以是和平或暴力的参与,可以是合法的参与或不合法的参与”。〔28〕持此种观点学者大多认为,将非法的政治行为排除出政治参与的研究范畴,会影响到中国语境下政治参与研究的完整性。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政治行为的合法与否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阶段是不同的,而且也是变动的。“参与行为的合法性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一定国别和历史时期下可能是‘非法的’、‘非常规的’或‘非正统的'活动(如示威和罢工),在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历史时期下可能就是合法的。因此,若排除非法的或制度外的参与行为,就会破坏研究的完整性,而且严重妨碍跨国的比较研究。”〔29〕其次,如何将非法的政治行为规范化和体制化,正是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主体之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将体制外的参与活动内化到体制内途径,使政治参与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尽可能降低暴力和无序参与发生的可能性,正是目前政治参与研究的重要课题;若将非法或制度外的参与活动排除在外,就等于无视政治参与途径不断转化、扩充的动态变化,易于导致研究的僵化和脱离实际。”〔30〕最后,我国的政治实践中大量存在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政治行为。“我将‘合法性’(lega)l排除出我的政治参与的定义,因为许多政治行为,比如利用消极怠工、送礼、以及有帮助的私人关系去交换利益,都被中国公民广泛使用,这些政治行为虽然是‘准合法’(quasi-lega)l的,但却是他们获得利益的重要形式。它们(准合法政治行为)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任何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参与的研究都无法将它们省略。”〔31〕第三,关于政府的和非政府目标的比较,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有着较大的不同。在绝大部分国外学者的眼中,政治参与涉及的范围应该局限在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范畴之内。维巴和尼认为,“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限定在对政府的参与上。……我们不打算描述和解释那些不具有严格意义政治性的,即旨在影响政府的参与模式”。〔32〕虽然亨廷顿在政治参与是否包含非法和动员的认识上与维巴和尼不同,但是在政治参与是否仅限于政府目标上却与后两者相同,“政治参与只是指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33〕而在孔齐看来,政治参与只是涉及政府范围的行为,因为“(1)政治涉及到权力和权威的关系。(2)权力和权威关系中的主要角色是国家的政府。(3)政治涉及到国家政府”。〔34〕与这些国外学者不同,研究中国政治参与问题的学者大多将政治参与涉及的范围做较为宽泛的理解,其中主要的原因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海外华人学者史天健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研究政治参与首先的一个困难就在于如何界定社会中‘政治的范围’(sphereofpolitics)”。他接着解释道,“中国大多数非农民(nonpeasan)t都是这个国家的雇员,几乎每一个发挥作用的组织和公司都与政府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附属于政府。……大多数政治行为也发生在在这些组织中”。〔35〕显然,史天健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中将“政治的范围”仅仅限定在政府的范畴内是不足的,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参与涉及的范围既包括政府的行为,也包括其他公民和组织的政治行为。与这种观点类似,王浦劬认为,“从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对象来看,它不只囿于政府决策,而是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同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在之后的解释中,他将这种界定的原因归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当中,不仅政府在起很大作用,政党和人民团体等也都有很多实际的政治功能。公民参加政治生活,毫无疑问应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36〕虽然国内学者对于政治参与涉及范围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大多都从中国具体的国情出发做了相对宽泛的界定。例如周少来认为,“从政治参与的对象来看,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党的各级组织具有政治性的公权力,因此,不仅针对政府的影响活动,针对各层级党的组织的影响活动也属于政治参与”。〔37〕再例如陶东明、陈明明认为,“从(政治)参与的客体上来讲,参与主体加以影响和推动的应包括政治系统中的各种决策活动,不仅是政府决策,也包括政党决策和其他政治团体的决策”。〔38〕
比较政治学方法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社会制度;文化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叠加;信息化使各种错综复杂的理念、资讯、情报、内幕等等充塞于各种媒体,因而,必然地使我们采用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逐渐失去效率。如何创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卓有成效地加强、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真正使正确的理论占领人民群众的思想阵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内容、方法、手段、模式、效果、理念等等是一个系统,本文则侧重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两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将其置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重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教育方法上,却是各有特色,美国奉行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注重潜移默化的柔性灌输,重视实践教育,更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在教育手段上,更强调隐性教育。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注重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更多的是理论教育直接灌输,重视宣传的作用,弘扬主旋律,是典型的显性教育。
二、研究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统一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也开始起步。这方面的专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理论。二是确定思想政治方法论体系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90年代初至中期的起步阶段,90年代中期至后期的发展阶段以及2000年以来的突破性发展阶段。由于条件的限制,文章对1990―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等,通过CNKI数据库用主题检索的办法并排除重复项后,显示90年代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在之后的几年中研究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越来越多,成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方面学术论文大量增加。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中美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以及研究深度的逐步加深,是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也是随着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我的逐步推广而开始发展和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是一致。
关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历程的代表性著作那就是冯增俊先生在93年出版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方面的专著。冯增俊先生在该书的第五章,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学校德育的的一些概况,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系统地、全面的了解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概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随着苏崇德先生在1995年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问世,学术界认为那是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从起点阶段迈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该著作从纵向、横向两方面对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情况从纵向和横向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介绍。
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在1997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其思想政治教育搞得效果显著。陈教授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美国制度、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现已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也成为进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石。
郑永廷教授于2004年编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基本概念而且对方法的理论基础、功能特点、历史发展等也做详细的阐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构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实施方法方法、反馈评估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同时书中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不仅应当深入研究我们党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努力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要系统研究中外古代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借鉴。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能在比较、鉴别中发展和丰富。”同年王瑞荪教授编著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本经典著作,书中明确说明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王瑞荪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其所以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才能从鉴别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的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律。”
通过研究发现现在我国思想政治学术界,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方法体系的研究不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但研究主要成果还主要是论文和期刊文章,专著较少。对于在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现状、特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并未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虽有一些共同和借鉴之处,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完善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这一观点的提出,有助于人们在认识和研究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能从更新的视角,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2]苏崇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3]陈立思.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比较政治学方法篇5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伪旧砦泄窝Х⒄顾峁┑姆岣坏乃枷胱试春途槎韵螅龆酥泄窝耆芄辉谘拔鞣降耐保远灾泄缁岷驼稳妗⑸钊氲难芯课。轿鞣秸窝В迪肿陨淼亩懒⒎⒄梗佣钪辗⒄钩瞿鼙泶镏泄壑怠⑻逑种泄幕褚约敖沂局泄缁岷驼畏⒄鼓谠诼呒闹泄窝А?/P>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比较政治学方法篇6
关键词:外交政策交叉研究比较政治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snyder)、布鲁克(henrybruck)和萨宾(burton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politics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taylor)和乔迪斯(david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utility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andmargaret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berry)、约翰(freemanjohn)和乔布(brian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barber)和乔治(alexander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主权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的方法来看:有的以国内结构为主、国际体系为辅;有的以国际体系为主、国内结构为辅;有的则是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并重。这些方法并无真正的优劣之分,因而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议题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显得就很有必要。外交政策议题可以按照对国际社会的敏感程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政治安全等议题;第二类是指经济贸易等议题;第三类是指文化宗教等议题。对国际社会敏感度越高的议题越需要在研究方法中重视国际体系因素。战争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传统问题,处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来自国际体系的危险因素感知并不相同,感知内容直接影响了国家选择战争的可能性。而感知内容又和国内结构相关,只有综合国内外因素对其研究才能解释和预测国家的战争行为。经济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后地位逐渐凸显,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已经超越了政治问题,几乎不存在不考虑国际经济体系而制定外交经济政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问题相比,文化问题的国内性更强,再加上国际文化体系还处于松散和不完善的状况,研究重心应放在国内结构上。此外,由于文化外交政策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于国际体系对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外交研究在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的结合中,可以以国内结构为原因变量,国际体系为结果变量。